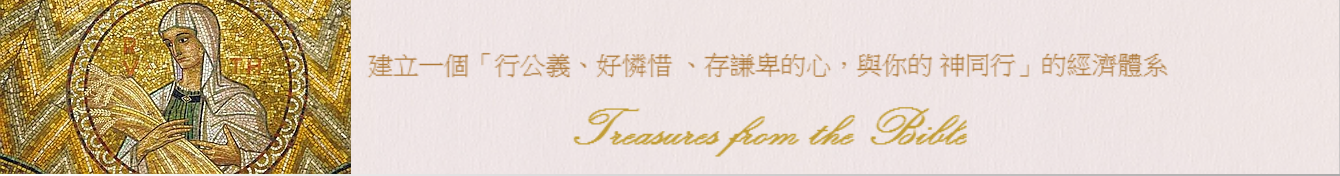凍省之後還要併縣市/蕭家興
凍省之後還要併縣市 [1]
或許是顧慮「統一與獨立」的政治敏感性,也或許是有意避開諸如:政治鬥爭、中生代卡位等陰謀論的過多政治聯想,國家發展會議不得不遮遮掩掩的將其「廢省」或「省虛級化」的共識,改口為「凍省」。而第二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也傀儡似的,在「先修治安,再談修憲」的抗議聲中,僅針對國家發展會議的共識部分作為修憲範圍召開修憲會議。作為臺灣人民的一分子雖然並不滿意,但也不得不慶幸,臺灣的政治環境終於由抗爭戒嚴體制的政治議題層面,轉到追求公共政策品質有關的行政體制的改造了。
「中央制定法制,地方依法行政」本為治權機關為相互制衡的組織設計,但目前臺灣這塊彈丸之地的行政體系卻分為四級,其中一級為制定法令的中央政府,另外三級則為執行法令的地方政府。依次為鄉鎮市(縣轄市)區公所、縣市(省轄市)政府及省市(直轄市)政府。較日本的一級中央政府及兩級地方政府:都(道、府、縣)及市(町、村),多出一級行政層級。即多出省市(直轄市)這一級地方政府,造成中央政府與省政府的轄區人口重疊百分之八十,轄區土地重疊百分之九十九,特別是省級政府的立法與執法功能不分,行政效率在公文依循體制下呈上轉下,甚至互相推諉,而耽延誤事。連帶的,在政權機關方面,立法院與省議會的民意監督功能,也存在重複問政及屢屢爭相抗衡,相互較勁的現象。
其實憑心而論,撇開公務人員的敬業精神有待再教育外,政府行政部門公權力無法發揮的一個重要因素,乃在於中央及縣市政府的編制人力,普遍不足以因應社會變遷的需要。故以「廢省」作為提高行政效率而論,本質上主要目的是要透過簡化政府層級免去省政府這一行政層級的二次決策,減輕不同行政層級間不必要的政策對抗,減縮無實質政策意義的公文呈轉作業,當然也減少省議會的二次議事作業來提高行政效率,落實權責一致的地方自治,而不是在於節約省級政府的行政人力。「廢省」的積極作法,應在於將省級政府的人力依法制作業及執行業務兩種不同工作性質劃分,歸併充實中央及縣市兩級政府的不足人力。
其次,在臺灣,縣市級地方自治單位的發展有兩個怪現象,其一是同樣是民選的地方縣市首長,其作為院轄市的地方首長的地位及組織編制,就比省轄的縣或市高一等;其二是鄉鎮級政府拼命鼓勵人口移入轄區,俾達到升格為省轄市或縣轄市的人口規模門檻。當縣轄市升格為省轄市,則另立與縣政府同級的市政府,實施「縣、市分治」。
目前行政轄區相互毗鄰的嘉義市與嘉義縣、台中市與台中縣、臺南市與臺南縣、高雄市與高雄縣等,即是本該同屬一個共同建設、共同生活的空間地域,卻分屬兩個不同的縣市自治單位管轄。此種「縣、市分治」的行政轄區劃分政策,只是增加了兩個互相推諉行政責任的地方自治單位,增加縣市議會數量及議員人數而已,對整體地域之共同發展及整體建設並無助益。反而因縣、市各自為政而無法共同解決道路、河川整治、棄土場、垃圾場與焚化爐區位等生活圈發展及建設問題。
特別是目前位於都會區發展的部分地方自治單位(諸如:臺北縣或基隆市)因行政層級不對等,而必須透過上一級地方政府(省政府),以對等行政地位及財政能力,來協調毗鄰地方政府(臺北市政府)共同解決城鄉發展及建設問題。甚且,有些諸如處於地形或經濟地理同質區域的嘉義與臺南、彰化與雲林,或是桃園與新竹等縣域,尚可基於農業建設或其他整體發展需要及行政的單純性作必要的行政轄區調整。長遠來看,配合東西向及南北向快速道路網及都會區捷運系統規劃,以較都會區發展範圍更寬廣的生活空間或地方生活圈,來規劃調整地方政府的行政轄區,諸如回歸日據時期的「州」的行政轄區,或是「大縣(已將毗臨的市併入)」的行政轄區,均較現行直轄市及縣(市)轄區來得符合地理空間經濟、都市建設及施政效率。
此外,長久以來中央政府行政部門最令國人詬病的,莫過於行政院的部會組織仍沿襲自舊中國大陸的中央部會體制,未能適應臺灣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重新通盤檢討、適當擴充及作必要的裁併,而是以疊床架屋的方式來建構無法自行擔當政策責任,而必須互相協調的的機關組織。諸如:行政院缺少名正言順的「建設部」組織,只有隸屬於內政部的「營建署」,且無視內政部營建署早就有一個具有法制作業實務,卻從無足夠人員編制的三級單位「公共工程組」,反而新設無法制作業功能,卻有較內政部營建署加倍人員編制的「公共工程委員會」;不裁撤或改組「蒙藏委員會」為「少數民族委員會」,而是疊床架屋新設「原住民委員會」……等等。
總而言之,要提昇行政效率,要改造政府組織體系,應不單止於「凍省」而已,在國民大會修憲「凍」省的同時,別忘了中央政府需要重新調整或裁併部會組織,而地方政府則需要配合城鄉發展,減縮縣市政府的數目,並重新劃分及調整行政轄區範圍。當然,在提昇民意監督效率方面,國民大會本身在總統已經由國民直接選舉,不必間接委由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的事實下,小小的臺灣實在沒有理由在中央層級仍存在「雙國會」的民意監督機關。故國民大會本身也理該修憲自我「凍結」或與立法院重新洗牌「合而為一」了。
[1] 本文刊於1997.5.25自立晚報「自立講堂」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