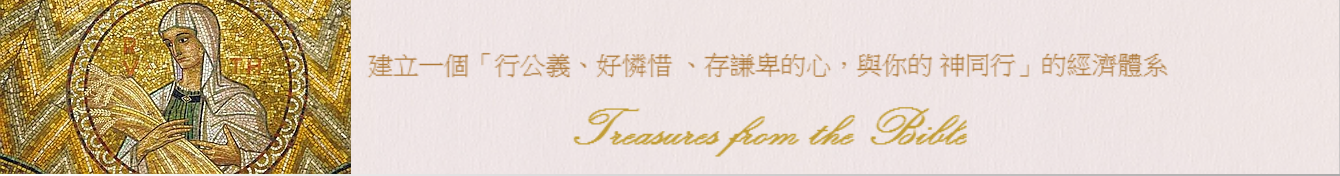天職觀與經濟倫理精神/蕭家興
天職觀與經濟倫理精神
天職觀(Calling)與經濟倫理精神可以說是清教徒(puritans)經濟生活的主要特徵。惟隨著入世禁慾主義的淪喪,清教徒事業的成功及世俗化,清教徒的天職觀及倫理精神遂發生重大的變化。
保羅的天職觀
保羅以傳道為終身事業,基於自覺是基督的奴隸,只有服從生命,不知要求報酬,故以製作帆布謀生為自發的副業(哥林多前書9::16-17),並充滿勞動的喜樂。
修道士與神祕者的天職觀
天主教教宗Gregalius一世把修道院的理想當作教會生活的中心,這種修道院運動屬於遁世出家式,無形中帶來輕視職業生活的危險,而且其重修道士的聖職,輕世人謀生的職業的二元價值區分,背離了天職觀的精神。其後的神祕家天職觀則給予俗世工作的勞動新的評價。認為從事最卑賤的勞動亦可達到最高的屬靈秩序。
路得的天職觀
路得否定天主教的二元秩序,而把職業天職化,認為工作與職業是神指定給各人的(哥林多前書7:17),信徒被呼召到各自的職業,違背神定的職業就是違反天意。對基督最美善的服事不是放棄俗世生活,而是在於接受職業作為天職,忠實地實行。
加爾文的天職觀
加爾文不把一切的職業看做天職,必須是對社會有影響、能服務鄰舍的職業才是神所接納的天職。認為職業非世襲的決定,而是以信仰的責任感來做自由的選擇。基督徒的天職在於要求積極的社會和政治的改革,獨一全能的上帝的主權與人類共同責任的主張,就是對政治與教會的專制猛烈攻擊。
清教徒的天職觀
清教徒的職業觀念轉變為天職觀可以說是由歐洲的宗教革命所引發的。認為人要在一項世俗的職業中去盡心竭力、持之不懈,有條不紊地勞動,為上帝做好管理工作。這種幾近以宗教觀念作為禁慾主義的最高手段的天職觀信念,是人對上帝真誠並從上帝獲得重生的最可靠、最顯著的證明。於是清教徒以自我奮鬥、勤勉奮進、忠於職守、精明強幹、全心全意投身於事業的創業精神、潔身自好、節制有度、嚴肅莊重的律法精神、講求信用、並固守著嚴格的資產階級的觀點和原則。
由於天職觀為經濟活動的獲利行為提供了合理的解釋,並且把人們在塵世中的工作,轉變成體現上帝意志的天職,終而培育了清教徒誠實守信、兢兢業業、忠於職守的敬業精神。認為賺錢是一個人責無旁貸的天職,只要賺錢掙得合法,就是長於、精於某種天職的結果和表現。
清教徒的倫理精神
特殊的宗教觀念對於經濟行為的影響就形成一種經濟制度獨特的「社會精神氣質(ethos)」。不同於中世紀天主教鄙視世俗生活,清教徒認為聖潔的生活只有通過與世隔絕的苦修方式來達到,清教徒認為這種放棄現世、逃避世俗責任是一種自私自利的行為,對榮耀上帝毫無價值。清教徒認為人係為了上帝而存在,要按著上帝的旨意做事。亦即,為「增加上帝的榮耀」,要根據上帝的聖誡來組織社會生活,以職業勞動為社會的塵世生活服務。故以愛上帝、愛他人與履行世俗的職業責任為己任。特別是宗教改革的「從世界中驅除魔力」的「使世界理性化」的過程,為清教徒的日常生活倫理賦予新的意義。
天職觀的轉變
初期清教徒的天職觀認為是一種回應主呼召的方式,主要是禮拜、日常生活及職業,社會服務是次要的。並警戒清教徒不要陷落於繁榮的泥沼,勞方及資方不可只求富有與幸福,進入上帝的生活才是正當的。
惟自1607年加爾文派的清教徒認為勞動是使人富裕,貧窮是道德的懶惰者。同時認為勤於天職的繁榮是上帝認可的記號,是引導進入天國的手段,並進而促進了經濟組織的產生以及產業主義抬頭,職業工作失去了信仰,逐漸偏離了基督教的倫理。原本順服家長的倫理,變成順服機器權威,勞動逐漸奴隸化,產業大戶無法滿足地榨取勞工的工資以致巨富。
禁慾主義倫理的轉變
清教徒承繼猶太人以上帝的選民自居的宗教信念,認為享有上帝特別的恩典,故其倫理觀念和日常生活往往充滿了對上帝感恩的情懷,故無不以能在此生中的勞動來回報上帝的恩寵。
清教徒基於人們在塵世只是受託付管理上帝恩賜給他的財富,任何人都沒有權利濫用自己名下的財產,信奉一種稱為「世俗禁慾主義」的職業觀和倫理觀,並發展出一種簡樸的帶有功利主義色彩的生活態度。
世俗禁慾主義倫理觀影響清教徒對於財富有節制的理性分配。對文化中任何不具備直接宗教價值的活動均懷有疑慮,甚至持敵視的態度,體育活動、文學藝術、戲劇娛樂、奓侈品的消費等都受到嚴格的限制。
財富觀的轉變
清教徒把通過工作追求財富看作是人的天職,把合理地擁有和利用財富看成是一種美德。把理性地獲利並合理地使用財富視為可以體現上帝在塵世的恩典,認為:獲利行為本身不是罪惡,追求財富本身也不是罪惡。
但當財富誘使人無所事事,沉溺於毫無節制的、罪惡的人生享樂之時,追求財富的行為才是不道德的、是邪惡的。或是當人為了日後的窮奢極慾,高枕無憂的生活或是為舒適的目的非理性地揮霍財產而追逐財富時,追求財富的行為才是不正當的。
追求財富的最終目的要能善用財富。使用財富必須是出於實際的需要或是某種理性的目的,才是無可指摘的。世俗禁慾主義倫理觀影響清教徒對於財富有節制的理性分配。特別是對侈品的消費給予嚴格的限制。
經濟倫理的轉變
宗教改革後,基督教的清教徒咸認每一位基督徒都從上帝領受有一種獨特的呼召,要他們義務地按照上帝所賜的才能,在他們所處身的環境中,各行各業中事奉上帝。
其次,十六世紀的清教徒在經濟倫理上,本質上係追隨加爾文的思想,相當關心貧窮的人,禁止高利貸,反對一切剝削、貪心,或致使他人窮困的買賣行為。這種入世禁慾主義使清教徒在事業上非常成功。
到了十七世紀,清教徒因事業的成功而導致經濟倫理的改變。清教徒開始認為事業的成就及財富的累積是蒙神揀選的印證,並且認為貧窮是上帝對懶惰人的一種懲罰,因此不必予以賙濟。這種錯用社會生產力提高,生活水準必然水漲船高的觀念,不僅在信仰行為上由「因信稱義」陷入「行為稱義」的偏差,終而導致對窮人漠不關心,也對盲目提高生產力導致自然資源枯竭、短缺,對經濟發展衝擊生態環境的問題視而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