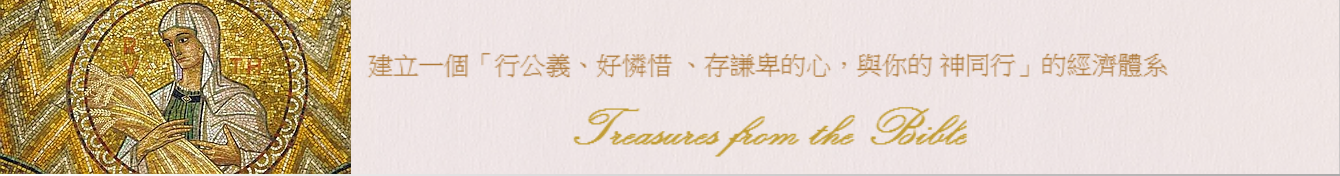第七章 從殉道到基督教/陳錦仕
第七章 從殉道到基督教
禧年的表現僅限於一世紀的教會嗎?我們有足夠的證據顯示教會在各個方面延續禧年的生活方式直到第四世紀。丟格那妥(Diognetus)的一封信,被認為是寫於二世紀,信中描述了早期的基督徒是這樣的:
他們僅像客旅一樣住在自己的國家。作為公民,他們凡物都與別人分享,但又像外國人一樣忍受苦難。每個異邦地土對他們來說都是自己的家鄉;而自家的家鄉彷彿是異邦他鄉。像所有人一樣,他們結婚生子,但是他們不殘害後代。他們共用一個餐桌,但不共用一張床。他們活在肉體裡,卻不順著肉體活。他們在地上度日,但卻是天堂的公民。他們遵守現有的律法,但同時他們的生命又超越了這些律法。他們愛所有的人,同時也被大家逼迫。他們不被人所知,但被定罪、處死又恢復生命。他們貧窮,卻使許多人富足;他們一無所有, 卻豐豐富富。(Mathetes,‘Epistle to Diognetus’,Chapter V, in Schaff, Philip, ANF01. The Apostolic Fathers with Justin Martyr and Irenaeus, http://www.ccel.org/ccell/schaff/anf0l.iii. ii.v.html)
從這封信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到了第二世紀,信徒們仍以一種激勵的、與眾不同的方式生活著。聖靈的同在很明顯,使他們的行為態度可以「超越」當時律法的要求。他們是另一國度的子民,但這沒有阻止他們不積極投入到周圍世界的需要去。跟隨耶穌的腳步,他們就是道成肉身的信仰。
他們對待物質產品的方法根植於簡單、團結、禧年慷慨的原則,「他們共用一個餐桌,但不共用一張床」。特土良在相同時期也寫到類似的情形,「大家都一心一意,對分享財產沒有任何猶豫。在我們當中除了女人(即妻子)之外,凡物都公用。自己與鄰居間設定的界限,全是因著聖潔而非貪婪的緣故。」
財產共有
這些被聖靈釋放得自由的基督徒,大方地贈與或與他人分享財產,為的是供給肢體中更缺乏的人,如孤兒、寡婦、在獄中的,甚至是非基督徒。光有什一奉獻還不夠,那時,舊約律法的規定已經被替代了。聖靈的到來激發了禧年慷慨,一種更「榮耀」的動力(參考哥林多後書3:7-11)。因為這是由愛而發,不是受律法的約束。
除了律法要求的什一奉獻之外,主還說,要把我們所有的與窮人分享。祂說,不單要愛鄰舍,也要愛仇敵;不單把財產贈送人與人分享,對那些奪走我們財產的人,也作個自由的奉獻者。(Irenaeus, circa AD 200, Against Heresies IV, xiv.3)
那些到教會來的人帶著錢和物—油、乳酪、橄欖、麵包和葡萄酒—作為他們的奉獻。窮人就帶來水,用來稀釋酒。到第三世紀時,也提到了衣服和鞋子。這些東西就放在入口的一個桌子上,由執事發給有需要的人,包括那些因各種原因沒有參加聚會的人。要記得,最初兩個世紀的基督徒中大部分是貧窮的奴隸。即使在他們當中,也表現出禧年的慷慨和財富分配。
我們不清楚實行財產共有的範圍有多大。但有一點清楚的是,直到第三世紀全體教會都在教導並操練財物共享。
凡物公用,富人也不應貪。一個人過著奢侈的生活,而許多人缺乏,這樣是不對的。將自己的奢華變成需要的人的歡樂,豈不是更榮耀嗎?將錢花在人身上而非珠寶上,豈不更明智喝?(Clement of Alexandria, Circa A.D.200, Instruction II, xiii.20.6)
讓強壯的照願軟弱的,軟弱的尊重強壯的。讓富足的服事貧窮的,讓貧窮的為這樣的人向神感恩,因為藉著他,自己的需求得滿足。(Clement of Rome, Circa AD 100, 38:2)
這些奉獻(放在教會財務內的)表明了人們虔誠的信心。奉獻不是用來花在酒會、筵席和晚會上的,而是為了照顧和供給窮人、失去財產和父母的孩童,還有老人、沉船的受害者,或因著教會的緣故在礦山上、在孤島上和在監獄裡的人—因著信仰,那裡成了他們的牢房。這種愛的行動在我們身上烙下了印記,別人看見就說:「看哪,他們是何等的相愛。」(Tertullian, Circa AD200, Apology XXXIX,5-11)
愛筵
另外一個在早期教會內表現彼此相愛關心的方式是愛筵(Agape meal)。
愛筵是教會整體生活的一部分。在使徒時代每天都有,到了後來每星期一次,邀請全部的人參加。與當今大部分的「服事」不同,初代教會的「服事」模式是,先是愛筵,隨後是講道,最後是聖餐。就像當時門徒和耶穌先是共用逾越節的晚餐,結束後才吃餅和杯;初代教會也是先享受愛筵,隨後才領聖餐。
愛筵有兩個重要的作用。以集體用餐和交通的方式,建造了基督的肢體;但至關重要的是,這樣可以確保那些比較貧窮的信徒至少每週一次能吃上一頓營養豐富的飯食。每個人都帶一些食物來和別人分享。不管那些貧窮的信徒帶來的東西多麼少,他可以隨便享用富人所帶來的一切食物。一部分食物也送給那些生病的和在家不能出來的。這就是保羅的異象—經濟koinonia:富人自願地照顧窮人的需要,以確保平等。這讓人想起當初以色列人在曠野分配嗎哪的方式(參考出埃及記16:14-18)。但是感謝聖靈的作為,人們出於自願而非強迫。
每個人按照自己的能力帶一些東西來。他們將所帶來的東西聚合在一起,然後坐下來共享。許多初代的基督徒生活都很窮困,有的還是奴隸。在希臘一個奴隸每天的口糧不到二斤的食物,外加幾個無花果和橄欖,還有一點葡萄醋。通常在每個主日吃到的食物,是他們一星期以來得到的最好的食物,也因著初代教會大家分享彼此所有的,他們才會吃到。如果我們裡面真有基督的靈的話,看到別人有需求而不去幫助,我們不會感到高興的。(巴克萊《神的年輕的教會》William Barclay ‘God’s Young Church’)
愛筵這個名字本身就解釋了一切。希臘文稱之為Agape 即喜愛。不管花費多少,我們都贏了,因為,愛筵可以滿足那些缺乏人的需求。(特土良 Apology XXIX16)
不幸的是,作為服事整體的一部分的愛筵為期不長。保羅去世後,敬拜變得越來越正式,而愛筵逐漸從主日的服事中被分離出來了。聖餐成了教會公眾生活的焦點。但是到了晚上,愛筵作為一個單獨的活動仍進行了一段時間。但是,就如保羅責備哥林多信徒那樣(參考哥林多前書11:20-22)—醉酒、貪婪、無秩序,最終使愛筵消亡了。
到第三世紀末,教會距離最初、非正式的樣子已經十分遙遠了。但有的學者認為這並不普遍。神職人員和平信徒之間的差別越來越明顯。教會開始獲取財產。不僅愛筵與聖餐分開,並且聖餐變得越來越程式化。教會的本質變得越來越像一個機構,這種潮流仍在繼續,朝著無法預見的方向發展。
君士坦丁大帝信主
早期基督教的顯著特點之一是,這是一種地下活動。基督教在羅馬帝國時期是屬於非法宗教,凡擁抱這信仰的人都會受到嚴重逼迫。許多人因此喪失了生命,其中最有名的一個故事是士每拿的主教坡旅甲(Polycarp西元69-155年)的故事。因他拒絕向凱撒獻祭、拒絕稱他為「神」,於是被綁在木頭上用火燒死。他的執行者最後一次命令他承認凱撒為神便可活命,但坡旅甲回答說:「我作主的僕人86年,祂從未虧待我,我豈可褻瀆祂?」
這樣英勇殉道的行為,在最初的三個世紀內是極為平常。但是,到第四世紀情況就改寫了。羅馬皇帝君士坦丁(西元306-337年)改信基督教後,突然之間,基督徒成了社會的主流。曾經沒有敬拜自由的基督徒,到了第四世紀,基督教不但是合法的,而且被宣告成為羅馬帝國的正統宗教。這對教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教會曾經一直被視為反正統的文化,現在更多的是符合文化。教會和政府變得越加密切地交織在一起了。教皇被賦予新的政治權力,而君士坦丁大帝也賦予自己很多神權。政府的財務用來修建精美的教堂並補助神職人員。富有的地主為生活在本區的人修建教堂,然後指定神職人員來管理。那些還沒有受洗的人,需按照國法的規定,接受關於受洗儀式重要性的教導。此後,仍拒絕受洗的人將受到嚴厲的懲罰。在這種強制的環境裡,名義主義不可避免地興盛起來。「教會」變成了建築物,而不再是基督的肢體。人們出席教會活動卻不屬於教會,作一名基督徒不再需要完全委身。對很多人來説,這只是權宜之計。
接下來如何維持這些教堂建築?還有那些教會擁有的土地,和那些神職人員也該怎麼辦?
到第五世紀末,羅馬教會已經設計出一個系統,將所有來自房租和奉獻的收入分成四部分—主教、神職人員、窮人、教會的維修和照明。其他地方分配方法各自不同。在這個體系下,主教的收入比牧師和執事高得多,不過他要將一大筆錢用來慷慨奉獻。另一個對比是窮富教會之間的比較。羅馬主教的財富多得令一位異教徒參議員Praetextatus說:「讓我成為羅馬的一位主教,我明天就成為基督徒。」而另一方面,鄉村神職人員的收入卻非常少,以致他們不得不依靠教會會眾的慷慨捐贈。(Jonathan Hill,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門徒們共用一個錢袋、初代教會經濟共享、保羅教導的經濟平等都已經被遺忘了。更糟的是,這些教導更被故意忽視了。有些教會豐富有餘,而有些教會卻是捉襟見肘。還有,許多剛信主的人很富有,但是沒人鼓勵他們應與他人分享財富。君士坦丁之前的教會,那種激勵共享財富方法已經被要求不高的方法取代了。穆瑞(Stuart Murray)在他的著作《超越什一》(Beyond Tithing)中總結了以下的變化:
神學家搜集了舊約和各種世俗哲學,發展了一套可以更廣泛地為教會所接受的體系。這個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是:
- 一個人實際的財富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對這些財富的態度。如果他不覺得自己被這些財富捆綁,那麼就可以保留財富。
- 奉獻的動機主要不再是出於對窮人的關心,而是對自己靈魂的關心。對一個奉獻者能得到的屬靈獎賞的看重,遠超過對窮人需求的看見。
- 認為奉獻給別人是一項很好的投資。以前認為這是過一種更簡單的生活,而現在被看成是神會因此增加一個人的財富。
- 愛筵團契(Koinonia)的概念被「施捨救濟」取代,關心窮人被看成是「慈善」而非公義。
- 教堂建築的維修、為教會領袖提供適當的經濟支援,佔據優先位置,剩下的錢可以分給窮人。
- 一些教會的領袖開始提倡什一奉獻。
即使在君士坦丁之前,教會一直有樂於助人的元素。在第三世紀中期,迦太基(Carthage)主教居普良(Cyprian),在他的著作裡曾仔細衡量是否該重新引進什一奉獻。但是君士坦丁的信主、教會和政府的包容,留下了一種不可改變的、對傳統態度的趨勢,是被大多數人接受,而被極少數人反對。神學家和牧師,開始以舊約中什一奉獻的規定(選擇性地),作為他們教導奉獻的依據。儘管是摻了水的教導,但畢竟是回歸到了律法上。新約的見證—五旬節所發生的事、保羅關於經濟分享的異象,漸漸被放棄了。
最初被定位是自願奉獻的什一奉獻,最終通過民事立法成為了強迫性奉獻。隨著教會擁有土地數目的增多,什一奉獻變質成一種納稅形式,才可維持教會的財產、設施、員工和官僚體系的運作。直到上個世紀,這種稅收在英國最終被廢棄(1936年什一奉獻法TitheAct),但是其影響直到今天仍產生作用。當傳道者講到奉獻的時候,更多引用舊約的什一奉獻模式,而很少引用新約的經濟共享模式。就早期國家教會而言,他們財務有多少是以直接忽略窮人的需要為代價,而用於教會的建築和其他的基礎建設?
這種方法的危險和悲劇不僅是忽視了聖靈的見證,又將我們帶回到律法之下,並且它也代表了一個削弱了能力的律法版本。什一奉獻在舊約中不是突兀而立的。它是禧年包裹中的一部分,每三年一次要將財物的十分之一帶到城中分配給窮人。當人們遺棄了聖靈引導的經濟共享模式,更喜歡舊約中的奉獻模式時,經濟公平這個禧年元素也無情地被忽視了。為什麼這一點如此重要呢?因為這是什一奉獻與禧年不同的關鍵所在。再次,我們看看穆瑞(Stuart Murray)在他的《超越什一》(Beyond Tithing)中所寫的:
什一奉獻,有固定的百分比,平等地應用在每個人身上。但是,禧年的實踐對富人和窮人來說有明顯的不同。什一奉獻是關於收入的問題,而禧年是涉及資本的問題。與禧年供應引起的社會變化相比較,什一奉獻是相對小範圍地對利未人和窮人的資源重新分配,並不能阻止貧富差距擴大。
什一奉獻本身不能解決任何經濟不公義的問題,最多達至一個相對緩和的效果。從最壞的角度切入,它算是起到了安慰奉獻者良心的作用,但卻使他並不認真地檢視自己對待財富和鄰舍的態度。同樣地,他資助了接受者,使接受者保持為慈善活動的原因,這樣他就一直是被壓制而不是被提升到一個平等的合夥人位置。今天,有些教會中比較貧窮的人(或家庭),連自己的房子都買不起,卻被教導關於教會領袖(甚至是神)的期待,要將他們的收入作什一奉獻,也許是用作教會建築基金。通常這些資金都服務於教會的「異象」或「使命」,但很少用來幫助會眾中更有需要的成員。
如果人們要自由地享受管理神的創造,他們需要公義而不是慈善。就如憐憫勝於獻祭一樣,公義也勝於慈善。一個是出於愛,另一個是出於責任,到第四世紀末,教會已經進行了一次很大的更新。人數增多了,地理疆界擴大了,社會地位被正式確立,權力也增長了。但是代價是什麼?教會還有那種激進的、獨特的達到經濟平等的方法嗎?她仍舊是世上的「光」和「鹽」嗎?君士坦丁以後發展的教會,慈善和責任似乎是他們唯一的要求。
(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