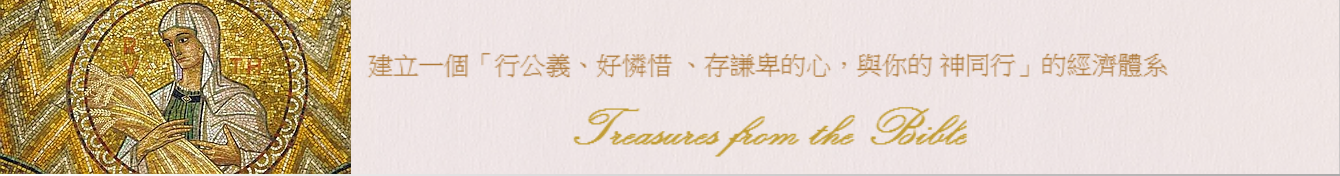位格與共融—再思AI浪潮中的教牧事奉/陳冠賢
位格與共融—再思AI浪潮中的教牧事奉
陳冠賢
中華信義神學院院長
早先個人的碩士論文用的就是neural network(類神經網路),勉強說稍微和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慧)沾到一點點邊。那時候的類神經網路所具備的學習功能,其實是非常有限的,不論是計算機的能力或是其他各方面,幾乎是沒有辦法做些什麼事情,專家系統就是當時早期人工智慧的一個程式系統。正如盧希鵬老師前面提到的,「這一切才剛剛開始而已」。所以,對於我個人而言,在這個起始階段想要提出一些較為深層的反省,此時是比較困難的。面對AI時代的來臨, 特別是AI背後可能帶來的一些神學省思,西方已有不少神學家有些不錯的著作,不過我今日並不特別從這個角度來探討,但會分享幾本不錯的著作及其論點。
一、AI浪潮背後的社會文化脈絡
AI(人工智慧)是電腦科學的一個領域,是新一代科技的發展,然而所有的科技其實是鑲嵌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脈絡當中。很多時候,我們大多只探究「科技本身」的技術發展,卻沒有留意到「社會文化脈絡」是不是也推波了AI浪潮?!
AI並不是在2006年Hinton教授發表演算法才開始的(值得一提的是,這的確帶來非常大的突破),而是在很早之前,人工智慧學習就已有兩大學派,其中之一的法則學派(Rule Based Approach)最主要的代表系統是「專家系統」,而「類神經網路」的技術則是協助「專家系統」累積歷次推理的經驗,以精煉其知識庫,進而改善專家系統的效率。甚至更早,在許多科幻小說裡就已經融合AI元素,反映了當時已經有人開始構想, 只是他們還做不出來而已。
也就是說,AI並不是一個突然出現的超級科技,它的發展一定有其背後的社會文化脈絡。當然,這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在今日研討會的有限時間裡,扼要分述如下。
(一)《縮時社會》與《在一起孤獨》
筆者為大家介紹兩位科技社會學家所撰寫的著作,以及他們提供的觀點和反省。作者在書中都隱約提及到AI,不過我們更需要看到的是,更大的一個社會文化脈絡。
1.《縮時社會》
首先,要介紹的是由茱蒂.威吉曼(Judy Wajcman)所寫的《縮時社會:奪回遭科技控制的快轉人生》(Pressed for Time: The Acceleration of Life in Digital Capitalism)這本書。
▎ 速度更快—工作更多—時間更少
「沒有最快,只有更快!」是筆者讀完《縮時社會》這本書之後的一個感想。現今社會正處於這樣一個「沒有最快、只有更快」的運轉之中,一切都要求快、快、快,我們人類對於速度的追求幾乎沒有停歇。在高倍速的效率之下,本以為能節省時間,其實反要負擔更多的工作,結果卻是可以使用的時間變得更少。
速度更快
筆者自退伍之後,1995年便服務於工研院機械所,鄰近工研院機械所旁的後面幾棟大樓是工研院光電所。猶記1995年筆者剛進工研院機械所時,工研院光電所裡有一支團隊spin off(分拆)出去創業。到了隔年,工研院光電所舉辦尾牙的時候,那支spin off 出去的團隊捐了汽車作為年終摸彩抽獎,以此回饋光電所。令人為之驚豔的是,他們捐了十部車!這是因為他們開發出當時讀取速度最快的光碟機。我想問問大家,現在你我的桌機或是筆電上,還有沒有光碟機這個東西?我想應該已經沒有了吧!但是在二十九年前,他們發表的光碟機讀取頭技術,是速度最快,更是領先全球業界的,甚至後來在1996 年,坊間還出版了一本暢銷全球的書,叫作《10倍速時代》。不過,現在大家已經覺得十倍速太慢了,因為我們對於速度的追求不只最快,還要更快!
工作更多
置身在如此高速運轉的環境之下,或許我們常常會覺得, 如果速度可以更快的話,似乎就能夠更快完成一些事情了!? 然而實際的情況是,提升更快的速度所帶來的結果就是要做更多的工作,並不會因為做事情的速度變得較快工作任務就會減少。
譬如在相同的距離下,如果我們加快速度的話,應該可以更快抵達才是,所以我們會覺得好像節省了時間。但是我們節省下來的時間不見得是你我自己可以使用,因為我們可能被賦予更多的工作,或者說,在同一時間內你我可能正同時進行著更多不同的工作。
時間更少
除此之外,還出現另外一個弔詭的現象,就是時間反而越來越少了。就連筆者自己也是生活在這樣一個現實當中。
今天早上(就是研討會當天),我從新竹搭七點二十五分的高鐵到台北,然後從台北車站搭捷運來到中華福音神學院的汀洲校區,應邀參加禧年基金會舉辦的研討會。結束分享後, 我預計十一點鐘離開,前往台北高鐵站搭車到高雄,因為今天在高雄聖光神學院,同時還有一場與信義神學院共同舉辦的研習講座,身為新任院長的我還是要到現場,所以我預計搭十一點半的高鐵直達左營,然後再搭計程車前往聖光神學院。試想,如果沒有高鐵的話,今天我就只能二選一,不是來華神這裡,就是去聖光神學院,因為有了高鐵(方便又快速),我好像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了。
於是就變成了在有限的時間裡,我要擠入更多的工作,然而並不會因為有這麼多的工具(有了更快的速度)使得我好像可以有更多可利用的時間了?並不是這樣的!面對接踵而來的更多工作,反而我要花更多的時間做預備,結果就是我自己可以使用的時間變得更少。
▎ 高速運轉的社會價值觀
因此,我們現今正處在這樣一個高速運轉的社會當中,而且這個高速運轉使得我們好像沒有辦法停下來。筆者實在不願意這樣說,但我們似乎是活在一個「速度崇拜」的社會當中無法停下,而且「速度」變成了一個「價值」,也就是「更快」意味著「更好」!
筆者曾在香港進修一段時間,所以那時候時常是兩邊飛來飛去。每次我從香港回來,剛好又有機會上來台北時,經常會有一個感覺就是台北大眾捷運系統其實滿舒服的,因為跟香港地鐵比起來,台北捷運的節奏稍微比較平緩,這是一種相對的感覺。其實我們已經越來越習慣於高速運轉的時代,像這些人工智慧或是相關的高科技產品,有時候不見得是為了(追求) 更快才發明的,也有可能是,當我們有一些其他的期待或者是這個工具(或科技)被發展出來的時候,它無意間就加速了, 使得我們就習以為常,甚至成了我們認同且肯定的一個社會價值,於是速度越來越快。
2.《在一起孤獨》
為大家介紹另外一位來自麻省理工學院(MIT)科技社會研究教授: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她著有《電腦革命: 人工智慧所引發的人文省思》(The Second Self:computers and the human spirit)、《虛擬化身:網路世代的身分認同》(Life on the Screen),以上兩書與《在一起孤獨:科技拉近了彼此距離,卻讓我們害怕親密交流?》(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構成三部曲。
作者投身科技心理研究超過三十年,在《在一起孤獨》中,她表達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也是她長期以來對於科技與人類之間的一個互動關係的理解,就是我們人類一方面仰賴科技來建立關係,同時又仰賴科技免受關係的侵擾。
▎ 以人造親密感克服孤獨
社會高速運轉之下,關係卻似乎越來越疏離,人們透過科技建立「人造的親密關係」克服孤獨,如電子寵物、智慧助理、照護機器人等,取代了原本人們所扮演的傾聽角色。
電子寵物(Cyber Pet)
曾經紅極一時的「電子寵物」(Cyber Pet)現今已不如往日了,回顧台灣的電子產業,過去有一段時間是以此為主業的。
還記得當年曾經風靡一時的「電子雞」嗎?當時有些家庭可能不太容易飼養寵物,有了這個「電子寵物」就方便許多, 它不僅可以隨身攜帶,也不怕把它養死,只需換掉電池重新啟動,它又復活了。另外還有一個稍微具體、仿真、聲控的「電子狗」也是如此,這一類的「電子寵物」提供了一種人造的親密關係。因為有些人可能不容易獲得卻又渴望擁有親密關係, 透過這類「電子寵物」,他至少可以建立一個人造的親密關係。
智慧助理(Virtual Assistant)
「Hi, I’m Cortana.」
「Hey, Siri.」
「Ok, Google.」
另外一個就是「智慧助理」,如微軟小娜(Cortana)、蘋果Siri和Google助理。大家有沒有留意到,呼喚這一類的「智慧助理」時,都加上了問候語(如Hi, Hey),有如我們吩咐或詢問「智慧助理」時,似乎已經將它視為一個諮詢者了。
就某方面而言,它也是一種人造的對話關係。前幾天,筆者看到一位在英國求學的朋友在臉書上的分享,也許是因為現在英國天氣很濕冷(尤其是冬天特別難捱),這位朋友希望他每天早上可以有一個神學對話的對象幫他醒腦一整天(提振精神)使他可以作研究。於是我開玩笑地對他說,你不妨上網去找找有沒有theology chat partner,就是神學對話機器人,或者用iPhone叫出「Siri語音助理」。當然這是一個玩笑話,不過正好反應出我們期望建立一個人造的對話關係。
照護機器人(CareBot)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照護機器人」(CareBot)比起前面的「電子寵物」,就更進一步肩負起照護的工作。「照護機器人」不僅可以陪伴這些子女不便照顧的長輩或獨居長者, 還可以跟他們對話,猶如觸動這些老人家心中溫暖的感覺。「照護機器人」不但能提供醫療照護,還可以療癒心靈,是一種所謂的人造的照護關懷。
更多時候,「照護機器人」是一個可以傾訴的對象。因為有些獨居長者可能已經找不到同齡的朋友(或許安息離世了),或是子女也都忙碌不太有時間跟他聊天話家常,此時這個「照護機器人」不僅可以扮演陪伴傾聽的角色,同時也可以偵測他的生理狀況,即時回報給醫療機構或護理照護機構,作為偵測異常狀況並預測意外之用。就某方面而言,「照護機器人」像是要以人造的親密關係,試圖去克服人們的孤獨與空虛。
▎ 貌似交流的相互連結
其次,雪莉.特克也提到,現代科技造成了另外一個現象,就是貌似交流的相互連結。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大家同桌吃飯,卻各自滑手機,更甚是,大家正用Line在群組上互傳訊息,意味著大家看似有連結,卻沒有實體交流。然而又不能說沒有實質交流,因為彼此正使用科技產品在進行交流著。
另一種情況是,因著科技發展,大家同步多工。在遠端使用通訊軟體溝通交流訊息的同時,手上也正忙碌於別的工作, 對於許多人而言,可能就是這樣忙碌著。在遠端彼此是有相互連結的,然而因為有空間、距離的因素,也造成了同步多工、貌似交流的現象。
3. 被數位資本主義馴服?
仰賴科技建立關係並保持距離
試想:使用AI的人,會不會被數位資本主義馴服?一方面仰賴科技建立關係,同時又與人保持一定的距離。
面對AI時代或是AI浪潮,其實我們大家都沒有辦法迴避。因為AI科技並不能從人們的生活中單獨排除或是個別思考,它就是在這樣的情境中被人們使用,同時它也影響生活在這情境中的人們。
(二)AI浪潮:克服或強化?
面對AI浪潮的發展,對於若即若離的人際關係,究竟要如何使用AI科技?是克服還是強化?筆者無意做任何預測,但我們的確需要留意的是,當我們在思考這些新科技帶來的影響時,我們不應該忽略這個社會的文化脈絡,雖然有時將社會文化脈絡納入考慮不見得立刻會有答案,但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留意這些科技究竟要不要強化或促進它?或者,我們是不是有可能使用這些科技嘗試去克服上述人際關係與交流呢?
二、再思位格與共融
筆者作為一位神學教育工作者同時也是教會的牧者,在AI 浪潮和社會文化脈絡之下,對於教牧事奉,還是回到兩個很古典的詞彙,一個是「位格」,另一個就是「共融」。
(一)三一認信:教牧事奉的前提
1. 內在三一:神聖三位格的共融
我們的信仰告白—三一認信,也正是我們教牧事奉的前提。就「內在三一」而言,我們所認信的三一上帝,是神聖三位格的共融。也就是說,我們所認信的是父、子、聖靈的共融,不僅是神聖位格者,更是一個至高無上而且至善的共融。
2. 外在三一:神聖三一與受造界的共融
另一方面,就「外在三一」而言,就是神聖三一的對外工作(包括創造、救贖、成聖),是神聖三一與受造界的共融。
不管對內對外,神聖三一都指向關係。因此,你我須回到「位格與共融」重新進行思考,因為教牧事奉的前提是回到「三一認信」上,也就是神聖三位格與受造界「存有關係」的共融。
(二)位格與共融:教牧事奉的特徵
對於教牧事奉,「位格」和「共融」是兩個很重要的特徵。
1. 重拾位格性
首先,你我要留意的是,重拾位格性。以盧希鵬老師示範的ChatGPT來說,它似乎可以做很多事情,乃至於生成式AI還可能發展出情緒甚至是意志,不過這只是人們對於位格的某種定義。難道這些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LLM) 的演算法,真是一個「位格者」嗎?雖然它可以生成各種文本、聲音、圖片、影像⋯⋯等,它還可以為我們生成禱文,但它並不是位格者!即使ChatGPT可以展現出比我們強太多的理性,甚至可以模擬出感情還有意志的決定,但它真是一個位格者嗎?絕不是的!所以,在教牧事奉中,我們需要留意的就是重拾位格性。
▎ 位格對位格(Person to Person)
教牧事奉必然是位格對位格(Person to Person),就是位格者對位格者。從信仰的角度來看,唯有三一上帝—非受造的「神聖位格者」—才能夠從無「創造」出「位格者」(也就是我們人類),而我們只能夠藉著上帝所賜給我們的生育能力「生產」出「位格者」。我們沒有辦法造出位格者,唯有上帝才能夠造出位格者,而被祂所造的位格者只能夠按著上帝所賜給我們的能力生育出位格者。
另外有一個爭議的議題,就是「人造人」,這是一個「生命倫理」的問題。過去,「人造羊」的議題已經對生命倫理產生很大的衝擊,何況是「人造人」呢!從「生命倫理」的角度而言,人們試圖想要逾越這個界線,想要如同(像)上帝一樣。創世記三章中提醒著我們,AI仍無法取代「位格者」。
▎ 位格與位格一同(Person with Person)
況且,這個位格者(就是牧者或弟兄姊妹)在服事鄰舍或是服事同為位格者的弟兄姊妹時,是因為這個位格者受神聖位格者(三一上帝)的揀選和使用。也就是說,所謂教牧事奉, 同時也是神聖位格者對著我們這個服事者以及被服事者,而且我們也與上帝這個神聖位格者,一同在服事。
AI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人類似乎越來越機械化或工具化, 使我們忽略了在教牧事奉中,位格者是以關係為本的特徵。
2. 重視共融
教牧事奉也要重視共融。正如前面提到,科技帶來人際關係的矛盾,人們既想建立並渴望關係,又要逃避關係。
▎ 已在共融中(in the communion)
身為牧者,筆者常常提醒自己:並不只是在完成這些教牧事奉任務,而是在與弟兄姊妹的共融關係中服事,也是在與上帝的共融關係中敬愛祂,並且受祂的差遣來服事同在這個共同體和關係中的弟兄姊妹。
▎ 朝向終末共融(toward the communion)
不僅如此,這份共融也指向永恆,是朝向末後的共融。正如我們在《使徒信經》中的信仰告白,我們相信耶穌基督將來必要降臨,審判活人、死人,而且末後我們都要從死人中復活,並且得永生。這個永生,並不是指我們現今的生命無時間的延續到永遠,而是指我們要與永生上帝處在一個永恆美好的共融關係當中。
(三)結論
正如上一篇盧希鵬老師提醒我們的,這一波AI(包含ChatGPT)發展才剛開始而已!接下來還有很多各種發展的可能性。對於這些新科技,雖然不清楚AI以後的發展,我們要多多留意社會文化脈絡帶來的可能影響和關係的互動是什麼。當然,還是要回到我們的信仰價值觀,謹慎地去分辨和認識這些新科技。我們未必要把AI「鞭數十,驅之別院」,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已經無法逃離它了。但是,我們要如何與AI共存在這個世代當中並且謹慎地運用?我想,我們仍然要尋求從上頭來的智慧。
(本文為「2023年11月4日禧年聖經經濟倫理研討會」之重點摘錄,邱華英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