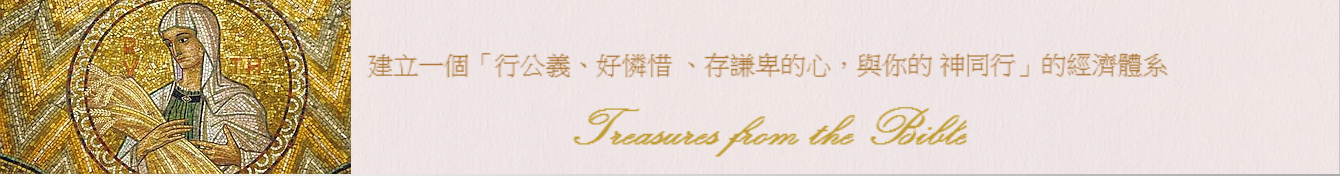公共財富與道德人性的奇妙關連
鄭仰恩(台灣神學院學術副院長)
斯密的自由經濟體系必須立足於以集體公民利益為基本考量的社會,才能發揮兼顧自利與他利的道德經濟力量。
本期《新使者》主題方向探討「信仰和財富的關係」,因為我今年進修假的研究計畫是「蘇格蘭啟蒙運動」,所以請容許我從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談起,再轉到他的道德人性論,最後才談二者的關係。
※ 亞當.斯密的一生
被譽為「現代自由主義經濟之父」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於1723年6月5日,出生於愛丁堡外圍佛斯灣旁的寇克卡迪(Kirkcaldy)鎮。他的父親讀法律,在當地海關服務,不幸於他出生數月前 因病過世。斯密的母親是位善良的基督教婦女,總是無微不至地照料年幼體弱的他,在寡婦和遺腹子之間有著深厚的情感,後來他也以同樣的愛心回報母親六十年之 久。他三歲時曾被一群補鍋匠綁走,雖於數小時後獲救,但幼小心靈必然受到衝擊。蘇格蘭自1707年起與英格蘭結盟後,沿岸走私猖獗,事實上這些私梟本是善 良百姓,為了生活家計才鋌而走險。從小觀察這些景象的斯密深深體認:利益當前,人們就會受本性驅使,不惜對抗官府。因此他在《國富論》裡提到:「人們潛藏 著改善自身情況的強烈本能…,光憑這一點,無須外力輔助,除了使社會繁榮富足,也足以剷除一切人為法律構成的阻礙。」這已指向經濟發展與人性本質的關係。
斯密從小接受優異的教育,因體弱多病,利用閒暇大量閱讀,善於分析思考。他十四歲進入格拉斯哥大學,最有興趣的科目是數學和道德哲學,後來上了哈奇森 (Francis Hutcheson)的道德哲學課程,從此改變一生。自格拉斯哥畢業後,他獲得獎學金到牛津大學的貝利歐學院(Baliol College)研讀七年,主要研習「斯文」文學(polite literature)及法文翻譯。因確信蘇格蘭式教育的優越性,他認為在牛津度過的七年窮極無聊,更形容該地大學是「頹圮體制與落伍偏見的庇護所」。他 因私下研讀大衛.休姆(David Hume)的《人性論》而遭教授譴責,或許因而離開牛津。斯密原本想當牧師,卻一直未正式擔任神職,1748年起,他在愛丁堡講授修辭學和優美文 學,1751年起,受聘為格拉斯哥大學的邏輯學教授,1752年,更接任哈奇森的道德哲學教席,教授自然神學、倫理學、法理學及政治科學等。他於1759 年出版第一本書《道德情操論》。
在格拉斯哥教學十三年後,他於1763年受聘為蘇格蘭首富巴克列公爵(Duke of Buccleuch)的私人教師,陪伴這位十八歲的小公爵及其弟到法國的土魯斯、日內瓦和巴黎進行歐陸之旅,不但親身觀察各地國情風土,更結識當代重要思 想家如伏爾泰(Voltaire)和主張「自由放任思想」的巴黎「重農學派」(physiocrats,或譯「自然經濟學派」)。1766年,因公爵之弟 感染熱病過世,他們結束遊學之旅,返回倫敦。在巴克列公爵終身薪俸的贊助下,斯密開始撰寫思慮已久的《國富論》。該書於1776年3月9日出版,獲得驚人 迴響,第一版於六個月後銷售一空。斯密的終身好友休姆對其受歡迎之程度大感驚異,不久,書中的理論也開始影響歐洲的公共政策。1777年,斯密悄悄地接任 蘇格蘭海關專員的職務,1787年更被邀聘為格拉斯哥大學校長。他於1790年7月17日死於寓所,墓碑上僅提及他是《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的作者。
※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觀點
《國富論》並非第一本以科學方法研究經濟的書,也沒有深刻的原創性觀點。它的最大貢獻在於首次通過觀察所得的證據,將當時許多不同社會的經濟生活放在一起加以 檢視,並以非專家的日常語言寫作,讓一般讀者易於瞭解。該書主旨可從其完整標題看出:《對國家財富的本質及種種成因之探討》(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在此,「財富」並非指金錢,斯密一再強調國家的財富在於商品(commodities),也就是那些可以使用及享受的物資。就像休姆以 及重農學派一樣,他反對重商主義者(mercantilist)所主張「國家財富是由國家獲取的金銀等錢財總額所構成」的觀點。他撰寫本書的目的是要顯示 國家財富的實況,並解釋它如何在現代商業社會中累積成長,最後提出持續該成長的政策建議。在分析不同經濟系統的運作模式和經濟成長史之後,他強調「本然自 由」(natural liberty)在這過程中的關鍵角色,進而提出「自由貿易」的主張,並批評重商主義者的保護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時也賦予政府提昇國家歲收及規範經 濟事務的角色。
採用牛頓的實證歸納方法,斯密以「勞力分工」作為基本詮釋原則,主張在勞力專業化且結合科技(包括工具和技巧)進展的情形下,經濟 就會藉助交易(exchange)而不斷成長。正如哲學思想會產生新的學門或科目,商品生產過程也會發展出新的科技或專業。另一方面,勞力分工的發展則會 受到市場範圍的限制。論到市場機制的運作,他討論商品價格起伏的因素,並論及「市場價格」和「本然價格」的區分和相互平衡功能。因為後者實際反映工資、利 潤和生產成本的價值,他依此發展出他的「分配」理論,並主張工資應反映實際工作的性質,工作若是勞累操煩、危險或是需長期訓練或報酬率低,工資就應相對提 高,如此工作性質的不對等就可以工資的不對等來加以平衡。
因為消費和累積資本(包括固定資本及流動資本)之間的複雜隨機關係,市場運作並不必然保 證財富的增加。有趣的是,斯密以人性心理學來探討經濟的發展。他指出,冷靜的「自利」(self-interest)動機會引導人進行交易、加入勞力專業 分工以減低勞累操煩,以及通過積蓄來累積資本以期追求更好的生活。在自利動機的交互運作下,人類社群獲得無預期且未經計畫的整體利益。他指出:「個人只在 乎自己的利益,但他卻被一隻無形的手引導促成一個原本非他所預期的目標」,亦即促進社會的總收入以及「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在另一處,他也提及,因為富人的消費及生活所需並不比窮人多出多少,前者的龐大屋舍和財產的經營維持卻能提供後者工作機會及生活所 需,這隻無形的手同樣引導富人促進社會需求的公平分配。
在此必須強調,斯密的「無形之手」理論並非嘗試將經濟學置於神學的基礎上,而是要指明那 「明顯且單純的本然自由系統」所產生的好處,是自然運作下的結果,非經個人或任何團體所計畫或操作。這就是他著名的經濟詮釋理論,主張一個理想的自然狀況 是全然公平而自由的。此一「自由放任」(laisses-faire)的主張,包含國際和本國貿易在內,主要是針對保護主義者的特定措施(譬如某些企業主 長期掌控見習生的作法)而發,希望商品的自由競爭和勞力分配的機動性不要受到不合理的限制。然而,斯密的論述總是帶著明顯的務實精神,強調必須將理想的方 案應用在現實世界裡。因此,他也認為保護主義者的措施在顧及國家安全和面對其他國家的保護措施時是合宜的。
※ 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觀點
斯密的《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一書嘗試給予道德判斷一個心理學的詮釋。十八世紀不列顛道德哲學分為兩派:理性派主張道德判斷應根據對道德原則的理性瞭解,實證派則 主張應根據現實世界裡的感官經驗。斯密確信理性派的觀點已經被他的老師哈奇森及好友休姆所駁倒,因此採取實證派的方法,但試圖超越他們的觀點。哈奇森從基 督教教義出發,但以心理學的觀察所得加以闡釋。他主張所有的道德判斷都是認同感或否定感的表達,而人類自然傾向裡的這種情感是一種可稱之為「道德感」 (moral sense)的天賦本能,就如同美感一般。道德的認同感是以「善意」(benevolence)為基礎,而道德的否定感則是源自善意的缺乏。這種「對他人 的幸福所產生的愉悅之情」成為我們判斷是非的依據,自利與他利在哈奇森的詮釋裡不再互相抵觸,而是在高層次的道德理念裡合而為一。
同為哈奇森之學 生的休姆於1734年出版《人性論》,並大膽地指出「理性總是臣服於感情」,而「私利」則是人類最底層的情感,因此,文明社會必須有一套疏導人類情感的機 制。他主張人性難以改變,但慾望本身卻可加以疏導,解決之道在於將人們貪婪的動機「昇華」為社會規範,並塑造一套「為大多數人施行公義及爭取最大利益」的 政治體制。這不必預設人心擁有內在的道德感,而是建立在「觀察者的認同感」上。也就是說,當一個人觀察到別人對善意行為的反應時,他的想像力讓他分享別人 所領受的快樂,這種同情心的感受成為道德認同感的基礎。
處於哈奇森「天賦道德感」和休姆「外在疏導機制」的分歧點上,斯密另闢蹊徑,並重新強調老 師所主張「可畏德行」(awful virtues)的必要性,亦即重視教義、自律、法紀,以及鄙視惡行之義憤的規範功能。他提出兩個具有原創性的論點:同情心(sympathy)以及「想 像的無私旁觀者」(imagined impartial spectator)。對斯密而言,同情心是一種社會想像力,通過他人的眼光來看出世界之不同可能性,進而引發對他人的認同感。這種「袍澤之情」讓我們產 生不忍見他人受難的惻隱之心,也是一種體驗他人苦樂悲歡的天賦本能。事實上,斯密的同情心很類似今日我們所稱的「連結感」(solidarity)或同理 心(empathy)。另一方面,想像的無私旁觀者指的是,一種在自身之外以他者的眼光來審視我們自身行為的能力,若將之定義為在人心深處有「別人在看著 你」的聲音,其實就是所謂的「良知」。這種自我評斷的能力,加上對他人的責任感,就成為道德判斷的基礎。換言之,斯密主張,道德加上想像力,就能建構快樂 美善的社會。
※ 在經濟發展與道德考量之間
表面看起來,斯密的兩本鉅著似乎沒有直接的關係,一本談經濟,一本談道德,主題相差 甚遠,但深思之下卻可看出二者的論述息息相關。這一方面當然和他所屬時代的學術方法論有關,因為當時在科學和哲學之間並無顯著的分際。另一方面,這也和蘇 格蘭啟蒙思潮緊密相連,因為對哈奇森、休姆、斯密和一整代的蘇格蘭哲學家而言,神學就是社會科學的一門,且總是和其他哲學或社會、自然學科進行對話,並共 同推動所謂的「公民人文主義」(civic humanism),亦即以公民社會的角度來關懷整體人性尊嚴與價值之提昇的運動。確實,對這些新時代知識份子而言,人類本就是社會性的存有,而他們無可 逃避的責任就是促成對人類處境的科學性理解和改善。
然而,歸根究柢來說,這個整全論述的關鍵還是在於斯密本身的思考架構。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分 析國家財富和社會資產的成長,或是探討人性本質與道德判斷的哲學基礎,他不但點出經濟發展和道德判斷的密切關係,更強調「同情心」所具有的社會功能。最有 趣的是,他總是將思考點提昇到「公共利益」和「他者觀點」的層面上。延續哈奇森所開啟的長老會人文傳統,斯密確信,良知不只是個人是非的考量,更是經濟互 利與公民社會發展的基礎。
伊恩.麥克琳(Iain McLean)以法國大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來詮釋斯密對現代世界的貢獻。首先,他指出,堅信「本然自由」精神的斯密不但是經濟自由主義者,也 是社會自由主義者,不惜一切掃除任何對自由社會發展的障礙。其次,承接長老主義創建者蘇格蘭改教家梅爾維爾(Andrew Melville)「信眾皆平等」的精神,斯密的信念反映激進的平等主義精神。最後,從他所一再強調的「無私的旁觀者」論點,我們看到一個具有社會主義精 神的博愛思想。(註)確實,斯密的自由經濟體系必須立足於以集體公民利益為基本考量的社會,才能發揮兼顧自利與他利的道德經濟力量。
無可諱言的, 斯密的思想有其時代性的限制,以他之名所發展出來的自由主義經濟體系更是弊病叢生,飽受批評。特別在現今個人主義盛行、自我意識高漲的現代資本主義消費社 會裡,他的自由經濟體系變得滿目瘡痍,窒礙難行。然而,他最大的貢獻在於以哲學理論為科學體系提供想像的架構,以補滿觀察所得資訊之不足和縫隙。儘管科學 體系日新月異,但這些哲學理論以及它們所蘊含的社會思維和道德意涵卻是日久彌新。
至今,許多保守派基督徒仍無法接受斯密(還有哈奇森和休姆)將道 德判斷與宗教信念切斷開來的作法,更嚴厲指責他們建構了一個無需宗教基礎的道德體系。然而,生活在現今後現代思潮與多元文化處境的我們,或許比較能夠體認 斯密所代表的時代新觀點。這應該也是一個重要的貢獻:就算不必以宗教為基礎,我們仍然可以建構一個追求自由精神和公平信念的社會。
註:Iain McLean, Adam Smith, Radical and Egalitarian: An Interpretation for the 21th Centu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20~132.